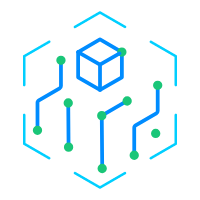华裔学生疯狂痴迷中学女老师十五年最终犯下恐怖罪行
华裔学生疯狂痴迷中学女老师十五年最终犯下恐怖罪行
华裔学生疯狂痴迷中学女老师十五年最终犯下恐怖罪行,美发师的苦,郑州美发用品,美发店充值活动 前一阵子去看了慕名已久的话剧《恋爱的犀牛》,坐在我左右两边的是两位陌生的男士。故事渐渐进入高潮,男主角对女主角表白道:
美发师的苦,郑州美发用品,美发店充值活动“我不会离开你,也不会让你离开我。你是哪也去不了的,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你找回来!别挣扎,挣扎没有用。我们注定要死在一起!”
我左边的男士幽幽一声唏嘘,显然是想起了一段缠绵悱恻的往事,我右边的男士则义愤填膺地骂道:
当然,文艺作品探寻的是一种极致的情感,不能用生活的准绳去丈量艺术(反过来也一样),若是在现实生活里,有人对你说“我不会离开你,也不会让你离开我”,那结局往往只有一片血腥。
这个小小的插曲让我想起41年前美国明尼苏达州女子玛丽·斯托弗(Mary Stauffer)的遭遇,以及它背后的恐怖主题:跟踪(stalking)。
跟踪这种行为,一般还被称作“缠扰”、“骚扰”或者“尾行”(日语)。在美国,有超过15%的女性和6%的男性遭遇过跟踪行为(CDC, 2014)。
我之所以用美国的数据,一是因为今天讲述的这个案件就发生在那里。二是因为它的统计数据比较全。但跟踪这种行为,全世界的模式都基本相同——女性的跟踪者们,将近九成是男性;男性的跟踪者们,则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。
这些跟踪狂里,超过60%是“死缠烂打”的前任和“没有安全感”的现任,有6%左右是亲属,剩下的则是那些“陌
最后这一种“陌生人”跟踪狂,也许是所有跟踪狂的故事里,最惊悚的一种类型,用“祸从天降”形容亦不为过。
虽然所有跟踪行为的恐怖指数和危险指数都很高,但其他类型中的受害者,起码还大致知道跟踪狂的身份,有可能能够避开自救。但对于那些“陌生人”跟踪狂,你则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,会在何时出现?
他们可能是和你有过一面之缘的客户、短暂接触过的同事、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邻居……
对你而言,他们不过是萍水相逢的过客;在他们看来,你却是他们命中注定要得到的。
玛丽·斯托弗的情况就是如此,当她的跟踪者最终现身时,他已经“迷恋”了玛丽15年之久,而她早已忘了他的名字。
玛丽·斯托弗本名玛丽·班戈(Mary Bang),1944年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杜鲁斯(Duluth)。明尼苏达被称为“北星之州”,民风友善淳朴,是美国地广人稀,气候最冷的地区之一,这也为日后此案中一系列的逃匿和潜藏,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
班戈一家有三个孩子,除了玛丽外,还有女儿桑德拉和小儿子汤姆。玛丽10岁那年,一家人移居到了明尼苏达的首府圣保罗(Saint Paul)辖区下的赫尔曼敦(Hermantown),玛丽在那里读完了高中,并于1962年进入明尼苏达的贝塞尔大学(Bethel University)继续学习。
贝塞尔大学创立于1871年,是一所私立基督教教育学府。1960年代初,全美只有6.7%的女性受过高等教育,考上大学并选择数学作为专业的玛丽无疑是一位非常优秀、很有想法的女性。
贝塞尔大学还有一个著名的神学院,专门培养神职人员(新教的牧师,可以结婚的那种)。那里有个名叫欧文·斯托弗(Irving Stauffer)的小伙子,他比玛丽大一届,来自玛丽的故乡杜鲁斯市。玛丽大二那年,两个年轻人成了一对甜蜜的小情侣,在贝塞尔大学1963年的年鉴上,还留下一张他们的合影。
照片里,玛丽展示着自己的胸花(美国传统,舞会上男士会送给心上人胸花),并用一道数学公式来证明“我如何爱你”。即使时隔多年,这张照片上依旧满溢着理科学霸的浪漫。这种浪漫也顺利修成了正果,玛丽毕业后不久,两人结了婚,玛丽·班戈也成了玛丽·斯托弗夫人。
1965年,玛丽大学毕业,欧文留校继续攻读硕士,玛丽则在明尼苏达的罗斯维尔市(Roseville)的亚历山大-拉姆齐高中(Alexander Ramsey High School)找到了一份教职,担任九年级(美国高一,相当于国内的初三)的代数老师。
虽然明尼苏达主要是北欧(30%)和德国人(40%)的后裔,但玛丽的班级里,也不乏其他族裔的学生,华裔学生薛明升(Ming Sen Shiue)就是其中之一。
薛明升生于1950年,来自中国台湾,家中还有两个弟弟。薛明升的父亲,是位林业统计学专家,曾任明尼苏达大学(University of Minnesota)教授。明尼苏达大学素有“公立常春藤”之称,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,可以说薛明升来自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精英家庭。
薛明升八岁那年,母亲林梅(音译)带着他和二儿子薛查理来到美国。薛明升的父亲买下了罗斯维尔市哈姆莱(Hamline)大街160号的一所小房子,一家人终于团聚。不久之后,林梅又生下了小儿子雷尼(Ronnie)。正当一切步入正轨之时,薛明升的父亲患上了癌症,在与妻儿团聚的第三年里撒手人寰。
父亲逝世后,薛明升成了实质上的“一家之主”。他颇有长兄的“威严”,经常暴打自己的两个弟弟。虽然薛明升谎话连篇,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,但却总是坚持自己有理,即使无故殴打弟弟,也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少年时代,他就出现了一些犯罪倾向,例如向车辆投掷石块,在陌生人的公寓里纵火。因为参与纵火,他14岁时就被勒令参加心理治疗。这个无法管教的大儿子令林梅害怕,她甚至形容他“没有感情,更像是一条狗”。
尽管如此,薛明升还是顺利地升上了高中。他的成绩名列前茅,还参加校橄榄球队和摔跤队,被公认为是很有前途的学生。
高中时代的薛明升,没再惹过什么麻烦,唯一的“不规矩”就是他似乎深深暗恋着自己的代数老师玛丽·斯托弗。
据说,班上有同学向玛丽老师八卦过薛明升对她的仰慕之情,玛丽对此只是一笑置之,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正处于荷尔蒙爆棚的阶段,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产生好感,也是人之常情。随着时间流逝,这种暗恋的火苗,大多会渐渐熄灭。薛明升也没做过什么不正当的“追求”举动,随着升上十年级,他也离开了玛丽的班级。
然而薛明升的“痴迷”并没有减弱,反而越来越强烈。玛丽老师很快替代了所有的电影明星,成了他性幻想的唯一主角。渐渐地,薛明升不再满足于头脑中的幻想,开始将这些“故事”付诸笔端。
这些“故事”的主题,一开始是你情我愿的“偷情”,之后逐步升级,变成了暴力的强奸和。当这些重口的幻想也无法满足内心的欲望时,薛明升决定,要将这些幻想付诸实践。
薛明升的幻想“升级”经历了几年的时间,当他决定采取行动的时候,却发现自己找不到玛丽老师的踪影。原来早在1967年,玛丽就和丈夫一道,离开了明尼苏达。
1967年,欧文·斯托弗(研二学生)和妻子一起,被派往菲律宾传教。这位见习牧师和他的妻子深受当地教众的欢迎。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欧文和玛丽,他们之后将在菲律宾的传教事业视作自己毕生的使命。
1971年,欧文正式成为了一名牧师,他和妻子被派往内布拉斯加州东部林肯市波克教区(Polk)任职。他们在这里度过了四年,并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,贝丝(Beth)和史蒂夫(Steve)。
然而两人并没有忘记初心,1975年,他们带着两个孩子,又回到了菲律宾,继续传教事业。
等到他们再次返回家乡明尼苏达的时候,已经是1979年,距离玛丽在拉姆齐高中任教,已经过了整整14年。
他的学业成绩一直很优秀,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后,他获得了奖学金,考上了父亲曾经执教过的明尼苏达大学,学习电子工程。不过薛明升很快就辍学了,决定先做生意赚点钱,再继续学业。
薛明升在明尼苏达大学旁边,开了一家名叫“Sound Equipment Services”的电器商店。一开始,这家店经营得相当好,后来日渐萧条(但总体来说还是赚钱的),然而薛明升却再也没有回到校园。
1973年,薛明升的母亲林梅再嫁了一个名叫默林·迪克曼(Murlyn Dickerman)的鳏夫,这位迪克曼是她的上司,也是个小有名气的林学专家,曾任美国林务局研究部的副主任。林梅再嫁后带着小儿子雷尼迁居到了华盛顿,留下来的大儿子薛明升和二儿子查理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。
虽然只剩下兄弟俩相依为命,但他们的关系非常疏离。据说,薛查理平日只能住在地下室里,和“楼上”的大哥几乎不打照面。薛查理的成绩也不错,同样考上了明尼苏达大学,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工作,结婚后就搬走了。
这所老房子便成了薛明升一个人的“地盘”,后来的一系列绑架和囚禁也都发生在那里。
据邻居们回忆,薛明升的父母是一对温良勤奋的夫妻,薛家的两个小儿子也属于外向友好的类型,都很讨人喜欢。薛明升则不和任何人交往,是个沉闷阴郁的“独行侠”,行事还有一股“狠劲”。
曾有三个劫匪闯入他的电器商店,将薛明升打倒在地,但他却带伤与他们枪战,将劫匪们打得一死一残(当然这属于正当防卫,他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)。
薛明升阴沉的性格令邻居们颇有点惧怕,都不太敢“管他的闲事”——这也导致日后他实施绑架和囚禁时,他的邻居们(甚至还包括回地下室暂住的查理)对此毫无察觉。
当然,他也没有停止“追寻”玛丽老师。1975年,他甚至找到了玛丽的老家杜鲁斯,持枪闯进了“欧文·斯托弗先生和太太”的家里。
然而,薛明升却搞错了,这位“欧文·斯托弗先生”是玛丽的公公(他和儿子同名),而“斯托弗夫人”则是玛丽的婆婆。气愤的薛明升将两位老人绑了起来,用枪指着他们的头,威胁他们不准将自己闯入民居一事报警。
两个老人没有报警,直到儿子和儿媳回国之后(1979年),两个老人才将这件事告诉了他们。两位老人和他人无冤无仇、儿子一家又多年居住海外,所以无论是他们、还是欧文或者玛丽,都猜不出这位“闯入者”的身份。
1979年,玛丽和丈夫从菲律宾回到了明尼苏达,住在母校贝塞尔大学的宿舍里。不过,他们这次回来只是暂居,牧师的派遣任期一般是四年,他们需要回国做一些继任程序。欧文和玛丽打算在1980年五月末返回菲律宾,继续他们的传教事业。
而此时,薛明升也获知了玛丽回美国的消息,他长达15年的“痴迷”之花,也结出了最恐怖的果实。
看到这里,很多人也许会非常不解:为什么薛明升会对少年时代没有私交,又多年不见的老师如此“执著”?这就要从跟踪这种行为的本质说起了。
虽然许多跟踪者都会以“执著的爱情”来粉饰自己,但跟踪行为的本质根本不是爱情,而是一种极端的控制。
当这种行为处于最初的“蓄力”阶段时(例如薛明升对玛丽幻想升级的时期),这时候的跟踪者,看起来和“偷偷爱着你”的单恋者,有那么几分相似。
但不同之处却在于,单恋者虽然也会幻想“如果我们在一起”,但他们清楚地知道对方不爱自己的事实,这也是单恋者万分痛苦的原因。爱情是需要“回馈”的,单相思代表着一种情感上的“无私”。
但是跟踪者却不然,在他们的心目中,对方可以不知道自己的存在,但两人“彼此相爱”却是一个不容辩驳的“事实”。
跟踪者通过幻想掌控两人“爱情故事”的走向,即使对方深爱别人/已婚/性取向不合,跟踪者也无动于衷,而这些对正常的追求者来说,都几乎是100%“劝退”的情况。
在跟踪者心目中,对方一旦知道自己的存在,就会抛弃所有,义无反顾地奔向自己。虽然经常有人用“钟情妄想”(Erotomania)来形容跟踪者,但其实大部分的跟踪者,都是神志清醒正常的——他们看似匪夷所思的“爱情妄想”背后,实则是狂妄的自恋。
跟踪行为的受害者们,都会有“为什么是我”/“喜欢我什么我改还不行么”的痛苦疑问,然而不幸的是,这种“天降横祸”往往是不可避免的,因为自恋的跟踪者们,早已将他们的“目标”物化(更确切地说,是猎物化)了。
他们“爱上“你的原因,也许只是因为你一个礼貌的微笑、一个不经意的回眸,可能因为你的长相、发色或者那天的衣着,甚至根本没有理由——因为一切,不过是他们自恋的投射。
你们的“爱情故事“,完全由他(她)来执笔,你虽然是名义上的“女主角”(男主角),却不允许拥有任何台词。
当这种幻想带来的兴奋感无法满足跟踪者的时候,跟踪行为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。跟踪者要将他们的“爱人”,强行拉入自己的幻想之中,一旦对方抗拒(必然的),跟踪者就会认为自己遭受了“背叛”,于是“报复”和“惩罚”便开始了……
他藏在玛丽家附近的树林里,一呆就是几个小时,甚至知道他们的备用钥匙放在哪里。他曾先后三次潜入玛丽家中,企图掳走玛丽,不过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,可惜这三次潜入都没有引起这家人的注意。
一方面是因为薛明升行动非常小心;另一方面,玛丽和欧文正为即将来临的菲律宾之行做准备,收拾行装、拜访亲友,忙得不亦乐乎。
只有一次,欧文注意到屋子的地板上,多了一些奇怪的木屑,案发之后他才发现,自己和妻子床下的地板,不知什么时候,已经被挖了一个大洞——欧文后来才知道,薛明升曾经打算挖地道将玛丽带走。
1980年5月16日,距离玛丽和欧文返回菲律宾只剩下几天时间。这天上午,玛丽先带着6岁的儿子史蒂夫到位于克利夫兰大街(Cleveland Avenue)的“卡门美容美发沙龙”(Carmen’s Beauty Salon)剪头发。之后她把儿子送到幼儿园。
下午4点30分左右,小姑娘剪好了头发,和母亲一起离开了美发沙龙,她们一边开心地有说有笑,一边走向停车的地方。玛丽开的是一辆73年的福特汽车,当她正打开客车位的车门,让女儿上车的时候,一个亚裔男人急匆匆地朝她们走了过来。
这人看起来30岁左右,戴着厚厚的眼镜,穿着打扮也算整洁得体。玛丽以为他是个迷路的焦急游客(因为亚裔在这个街区并不常见),于是友好地问道:“我有什么能帮你吗?”
然而回答她的,却是黑洞洞的枪口。男人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,直指着贝丝说道:
玛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尽量用温和友善的语气对这位劫持者说道:“我们都是基督徒,我们的上帝,他会帮助有困难的人的。我可以帮助你……”
在男子的逼迫下,玛丽将车开往安诺卡郡 (Anoka County)的偏远林区,这个过程中,男子一直用各种方式恐吓和威胁她们。
比如,在开车的过程中,他们曾停在某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,有一辆警车偶然出现在他们车后,劫持者就威胁玛丽,如果这辆警车再和他们一路,他就“一枪崩了贝丝”。
到了人迹罕至的林区,男子将玛丽和贝丝捆绑在一起,强迫她们脸朝下躺进这辆福特车的后备箱。
接下来(下午6点30分左右),男子在罗斯维尔郊区一个停车场附近停下车,准备将玛丽的这辆福特,换成自己停在那里的面包车。
这两个小男孩中的一个,名叫杰森·威尔克曼(Jason Wilkman),走上前去一探究竟。他刚刚礼貌地说了声“你好”,就被男子一把抓住,也扔进了福特车的后备箱里,紧接着男子开车疯狂逃离了现场。
另一个小男孩(他没看见后备箱里的玛丽母女)吓得跑去找杰森的妈妈,她急忙赶了过来,但车子早已消失了踪影,杰森的父母立即报了警。
男子开车驶向荒无人烟的卡洛斯·艾弗里野生动物保护区(Carlos Avery Wildlife Refuge),后备箱里的三个受害者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,这个男人又会将他们带到哪里。
玛丽试图安抚杰森,不断地和他说话,但这个小男孩吓懵了,除了自己的名字(杰森)和年龄,他无法提供任何其他信息。
汽车此时开进了山区,在路上剧烈地颠簸着,杰森哭了起来,说自己要回家,因为周末还要去看自己的外婆呢。贝丝也想起,自己这个周末也打算去看外婆。两个茫然又害怕的孩子,都伤心地大哭起来。
这时候车子停了下来,男子打开了后备箱,贝丝记得,他从自己身边取走了一根长长的金属棒——若干年后,她才明白,那是一根撬棍。
男子抓着杰森走进了森林,在那里,他用这根撬棍将这个六岁的小男孩活活打死。
很久之后,男子才回到了车里,他再次驶向那个停车场,丢掉了玛丽的福特汽车,将玛丽母女俩押进自己那辆黑色的、没有窗户的面包车。
他先将她们带到自己的电器商店,给她们一点果汁喝,又让她们去了洗手间。他告诉玛丽,自己已经将那个小男孩放走了,接着便命令母女两人蒙上眼睛,再次将她们塞进面包车,借着夜色的掩护,驶向哈姆莱大街的那所老房子。
进屋之后,他用自行车的锁条将母女二人锁在一起,关进卧室的壁橱,从外面锁上了壁橱的门。
这个壁橱长4英尺(1.22米),进深21英寸(53厘米),里面没挂任何衣服,只有毯子、两个小抱枕和一些塑料袋,橱柜上方有一只自行安装的灯泡。
当天夜里(其实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),男子在客厅地板上铺上一张毯子,将玛丽带出壁橱,蒙住了她的双眼,将她捆绑在一件家具上,并打开了一旁租来的录像机。
接下来是一段长达三个小时的录像“采访”,在男人一点点的“提示”下,玛丽·斯托弗才终于认出了劫持自己的人:他叫薛明升,是自己15年前的学生。
薛明升告诉玛丽,因为她给过他的一个B的成绩,让他无法获得奖学金,没能上成大学,结果他被迫征召入伍,参加越南战争,并被越共抓进了战俘营。他人生中的所有失败,全都归咎于她。
当然,这些所谓的“失败”,全是薛明升的谎言:他整个高中最差的成绩也是A-,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,不但得到了奖学金,还上了大学,从未去过越南(他是高度近视,军方也不会要他)。
他这些连篇的谎话,也和他少年时代的种种恶行一样,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,却还要坚持自己有理。换句话说,一切都是玛丽的错,而他想要的,不过是“报复”。
“我想你应该能猜到。我不希望你的伤疤是身体上的,我希望它们是情感上的。我想让你感觉肮脏、堕落和低贱。”
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,薛明升反复强奸玛丽,并把强奸的过程,全都录制了下来。第二天,他取出录像带,把录像机还了回去,但他对玛丽的性侵,却没有停止。
与此同时,玛丽的丈夫欧文心急如焚。本来,16日这天晚上,他们约好了和玛丽的姐姐桑德拉一家聚餐,然而妻子和女儿却一直没有回来。欧文先给美发沙龙打了电话,却被告知两人早已离开,他又找遍了附近的大小医院,但依旧不见妻女的影子。于是午夜时分,他打电话报了警。
警方当时正全力调查小男孩杰森的“绑架案”,过了一两个小时,才终于有个警察来到了他们的住处。他敷衍地问了欧文几个问题,认定这事不过是夫妻吵架,根本没把欧文的报警当回事,很快离开了。
直到18号的早上,警方在搜查杰森被绑架的区域的时候,发现了玛丽那辆福特汽车掉落的牌照,这才将两起案子联系起来。明州的警方又通知了FBI(因为涉及儿童绑架),接下来,多达300名警官和志愿者,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地毯式搜索,然而一无所获。
警方和FBI都将欧文视为首要嫌疑人,怀疑他杀害了妻女,反复对他进行调查和审问。
虽然这番操作现在看来纯属误判和浪费时间,但在当时来看,他们的怀疑也不无道理,因为根据目击者(和杰森一起玩耍的小男孩)的描述,嫌疑人的长相和欧文的确有那么几分相似(都是黑头发、戴眼镜)。
甚至当警方把这张“嫌疑人的素描”刊登在报纸上,向社会各界征集信息的时候,还有不少义愤填膺的“知情者”给警方打电话,言之凿凿地声称这位牧师就是凶手……
在通过了一系列测谎和调查之后,欧文终于暂时澄清了自己的嫌疑,但这却让警方更加一筹莫展:玛丽人缘非常好,无论和公婆、父母还是姐弟,全都关系和睦,又刚刚从海外归来,如果凶手不是丈夫,那么哪来的仇家呢?
这段时间对玛丽的家人来说,无异于地狱般的日子,每当附近发现了和玛丽或者贝丝年龄相近的无名女尸,欧文就要去“认尸”。
薛明升则过着两点一线的“普通”日子,他每天照常去电器商店,每晚按时回家,没人知道全市都在寻找的失踪的母女俩就被囚禁在他的壁橱里。
他几乎每天都会性侵玛丽,有时会长达好几个小时,但玛丽最害怕的是他会把魔爪伸向女儿贝丝,她恳求薛明升,请一定放过自己的女儿。薛明升则鄙夷地告诉她,自己才不是什么恋童癖,他也果真没对贝丝下手,强暴玛丽的时候,贝丝也都没有在场。
但薛明升很擅长以贝丝为筹码来胁迫玛丽。比如在强暴过程中,如果玛丽表现得不够“爱他”,之后薛明升就会抓住贝丝,将她塞进一只大塑料袋里,然后对玛丽说:
他去工作的时候,也只将玛丽一个人锁在壁橱里。他会把贝丝带走,塞进一个纸盒,反锁在自己的面包车里,在闷热的夏天里一锁就是八个小时(贝丝日后觉得自己竟然没死是一个奇迹)。
他算准了,玛丽不会抛下女儿独自逃走或是求助。而贝丝也同样不敢逃跑,因为薛明升告诉她,只要她不见了踪影,他就会立即杀掉她的母亲。
在薛明升的逼迫下,玛丽先后给丈夫欧文写了两封信,第一封说自己没有失踪,只是离开了他;第二封则强烈“建议”警方停止参与,否则自己将永远不会再出现。这两封信都被FBI拿去“分析”,但直到玛丽最终逃出了薛明升的魔掌,FBI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……
也许是自满于自己完全骗过了警方,也许是因为玛丽母女比较“乖巧”,薛明升渐渐放松了“管制”。虽然仍被锁在一起,但玛丽和贝丝被允许到楼上的厨房吃饭(之前吃喝拉撒都在壁橱里),每隔十天,她们可以洗一次澡。
他还让贝丝看电视,还给她买了一副桌游,用一种诡异的怜爱语调,叫她“贝茜”(贝丝的昵称),仿佛他是一个疼爱女儿的父亲。贝丝回忆说,她当时只觉得这种叫法很恶心,但事后回想起来却令她感到毛骨悚然。
在劫持玛丽和贝丝一个月后,薛明升要去芝加哥参加一场招聘会。他竟然租了一辆房车,带着玛丽和贝丝,顺便进行了一次“公路旅行”。他甚至带着她们,到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一家百货商场去买衣服(自从被劫持,玛丽和贝丝就没换过衣服),以便装成“一家人”的模样出行。
在商场里,他紧紧控制住贝丝,所以玛丽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,不过她仍然想方设法地求救。她用一张旅行支票付款,希望银行能够通知相关执法部门。
玛丽失踪后,欧文立即就将妻子手上有旅行支票这件事,告诉了FBI。但显然,FBI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,也没有嘱咐银行关注这张支票的使用情况。玛丽的这个求救信号,也便如石沉大海,无人回应。
还曾有一次,贝丝被短暂地一个人留在房车上(当然是被捆绑着),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刚好路过,她勇敢地爬到窗口,用尽全力向他们高喊:
男孩们却爆发出一阵恶毒的嘲笑声,告诉她“别再编故事”,而后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
在这之后,薛明升越发胆大起来。1980年7月4日(美国国庆节)这天,他甚至带着玛丽和贝丝去了科莫公园(Como Park),然后去一家餐厅吃晚饭,之后还到明尼苏达大学圣保罗农业校区看焰火。
玛丽回忆说,一路上她们至少看到了三辆警车,但她依旧不敢呼救,因为薛明升一直用枪抵着贝丝的后背。
被囚禁期间,玛丽每天都会给女儿讲述圣经故事。虽然得救的机会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和她们擦肩而过,但她依旧告诉女儿,要保持希望和信心。
1980年7月7日,玛丽和贝丝已经被劫持了整整53天,这天早上,薛明升告诉玛丽,他准备卖掉这栋房子,买一辆露营车,然后和母女二人“周游美国”。
一旦离开明州,那么她们被找到的几率就更是微乎其微,玛丽意识到,这是她们最后的机会了。
由于玛丽母女最近的“良好表现”,薛明升不再将她们分开,也不再将她们锁进壁橱里,而是先将她们两人绑在一起,再用另一条锁链,将她们绑在壁橱的顶端,之后以锁链的长度为半径,允许她们在卧室里进行“自由活动”。
薛明升去工作后,玛丽回想起小时候父亲的做法,用一根之前偷藏的发夹,卸下了壁橱门折页上的销钉。
接着她拔出销钉,那条绑在壁橱上的锁链随之掉落(但她们身上的锁链还在),玛丽抓住女儿的手,对她说道:
玛丽在卧室里,找到了一个干洗店的标签,上面写着:罗斯维尔市哈姆莱大街160号。这时她才终于知道,自己被囚禁的这栋房子究竟在什么地方,而这里距离玛丽自己的家还不到6英里(9.66公里)。
母女两人不住地发抖,感觉每一秒后薛明升都会回来,仍被绑在一起的她们,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楼上的电话机旁,拨通了拉姆齐县治安官办公室的电话。
电话却被挂断了两次,直到第三次,一个名叫迈克·福勒(Mike Fowler)的警长,才终于来到了电话机旁。
“我是玛丽·斯托弗,雅顿山(玛丽母女被劫持的地区)绑架案的受害者,我希望有人来接我们。”
不久之后,欧文也从FBI那里(他们此时还在“分析”那两封信),得知妻女获救的消息,连忙带着儿子史蒂夫,赶到了警局。
玛丽回忆说,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史蒂夫的裤子短了。在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,小男孩悄悄地长高了,而他一直活在恐惧和忧虑里的父亲忘记了为他添置新衣。
薛明升先被带到拉姆齐县的拘留中心。在这里,他让自己狱友理查德·格林(Richard Green),帮助他杀死玛丽和贝丝(格林即将出狱),以防止她们在法庭上指控他,并向他许诺五万美元作为报偿。然而,格林把这件事告诉了FBI(当然一开始并不情愿),薛明升的“灭口计划”没能实现。
1980年,薛明升以涉嫌绑架罪和强奸罪第一次受审。在玛丽出庭作证的时候,薛明升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,冲向证人席上的玛丽,幸亏检察官汤姆·伯格(Tom Berg)手疾眼快,一把抓住了薛明升。
薛明升的第二项指控,是对小男孩杰森的绑架。杰森的父母在儿子失踪的五个月里经历了地狱般的折磨。因为至今没有找到杰森的尸体,检方无法以谋杀罪起诉他。最终经过杰森父母的同意,检方和薛明升达成了认罪协定,检方同意不以一级谋杀罪起诉他,以此换回杰森的尸体。
1981年10月下旬,在薛明升的指引下,FBI终于在卡洛斯·艾弗里野生动物保护区寻回了杰森的尸体,此时离他失踪已经过去了166天。
在薛明升被控杀害杰森的审判中,玛丽需要再次作证。在她出庭作证的时候,薛明升突然跳过桌子,用一把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带进法庭的尖刀狠狠割伤了玛丽的脸。玛丽被紧急送往医院,伤口上一共缝了62针。
虽然薛明升的辩护律师试图以精神失常为他辩护,但心理评估显示他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。在这项审判中,薛明升因二级谋杀罪和绑架罪被判处40年监禁。和之前的30年刑期叠加在一起,薛明升需要服刑70年。
自始至终,薛明升都毫无悔意。他威胁玛丽,只要他有出狱的那天,那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她,如果她死了,那他就杀掉她的孩子。
2010年7月6日,薛明升获得了假释资格,不过阿诺卡县地区法官珍妮·贾斯珀(Jenny Jasper)拒绝了他的假释申请,裁定薛明升仍对社会构成威胁,他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。
1981年,玛丽伤势痊愈之后,她和丈夫再度回到了菲律宾,继续追求他们之前被打断的梦想和使命。
玛丽把这段遭遇视作自己生活中的一段“劫难”,劫难虽然可怕,然而它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,它无法毁掉未来,生活仍会继续。
玛丽的后半生无疑是美好的,她和丈夫欧文白头偕老。随着一儿一女双双结婚生子,他们也幸福地晋升为(外)祖父母。
从菲律宾光荣退休之后,玛丽和欧文又回到了美国,定居在赫尔曼敦的老房子里。在那里,玛丽度过了少女时代、考上了大学、与丈夫欧文初次见面。虽然已是满头白发,玛丽·斯托弗依然美丽动人。
贝丝如今也已长大成人,她终于明白,当年的母亲曾为她做过怎样的牺牲。虽然在她们获救之后,母亲就曾告诉她薛明升对自己做了什么。但直到几年以后,贝丝才真正明白这些话的含义,并因此愤怒了很长时间。不过贝丝从怒火中走了出来,她在一次采访中说:
“我不觉得自己是可怜的受害者,没错,他当年的确伤害了我,但我早就走出了那段阴影,我可以恋爱、结婚、生子,过我想过的生活。而他的余生都要烂在监狱里,他才是可怜的那个。”
杰森一家在此案之后基本上拒绝了所有的采访。对于纪录片和电影,他们都没有发表评论。薛明升在2010年申请假释的时候,杰森一家已经离开了明尼苏达,没有出庭,他们通过杰森的舅舅了解情况。
薛明升的假释被否决后,杰森的舅舅代表杰森的父母,告诉薛明升的母亲,他们一家已经原谅了薛明升。
对于薛明升的假释被拒,玛丽接受了采访。她表示,虽然自己和女儿贝丝早已努力将那段“劫难”封印在过去,继续她们的生活。但薛明升的假释被拒,对她们和家人而言,依旧是个“解脱”。
截至目前我没有发现她的讣告,所以这位现年78岁的伟大女性一定和她的家人一起,仍然低调、努力而勇敢地生活着。
相关文章
- 涉疫地区返回不报备!焦作王某娟隔离费用自理!沁阳、孟州多家门店被关停!
- 35岁的去学理发靠谱不 只要愿意学其实不晚
- 汕头怎么选择一家美发学校学美发要学多长时间多久?广州托尼盖美发学校 原创
- 男闯达拉斯美发沙龙 枪击3韩裔女 尚无仇恨犯罪证据
- 当你老了一生最后悔什么?全球统计前五名公布
- 小手指精选排行榜单无锡美容美发
- 分类曹县信息港2023年2月9日最新便民信息
- 济宁市泗水县济河街道金裕社区开展 “暖心理发 卫生大扫除”志愿服务活动
- 宁波纤手美发学校瑞美发制品
- 缇庡彂妞?甯稿窞鍝璐ㄩ噺濂斤紒
- 广州施华蔻美发连锁有限公司
- 日本美发店神奇魔镜可预览发型 智能高科技镜子售价5万元
- 【丝雨美容美发加盟】
- 安徽男子烫头被告知有毛囊炎 最终消费三千多 店家: 你又不是小孩子
- 2022年邻水县职业中学招聘汽车维修工、钣金喷漆工及理发师公告
- 曝光!近日月子会所、美容美发店、教培机构都爆出门店跑路、维权等新闻快来看看吧
- 第46届世赛美发项目中国集训队开始集训
- 27岁名校英语硕士缺爱嫁给初中生理发师婚后生活一地鸡毛
- 歌威洗发水合肥美发拉客
- 务请注意丨6月13日疫情动态